还记得第一次拉坯成功时的狂喜,捧着那个歪歪扭扭的茶杯,像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窑里,守了整整一夜。可当窑温冷却,打开窑门的那一刻——它裂了,从中间齐刷刷裂成两半,那声音清脆得让人心碎。
我不信邪。调整了泥料的配比,把坯体做得更薄、更均匀。第二次开窑,裂痕像蜘蛛网般爬满了壶身。第三次,壶嘴直接掉了下来。第四次、第五次……那些个月,我的工作室成了“陶器坟场”,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失败的残骸。有朋友开玩笑说,你这是在烧制“破碎美”吗?我只能苦笑。
最绝望的是那个雨夜。我花了三天三夜精心雕刻的南瓜壶,在出窑时发现壶盖裂了一道细纹。就那一道纹,整个壶就废了。我坐在窑前,雨水敲打着铁皮屋顶,看着那些裂纹,突然就哭了。不是委屈,是深深的无力——我明明每一步都按照书上来,为什么就是不行?
转机出现在去找老陈的路上。老陈在邻县山里烧窑,七十多岁了,他们家三代都是烧窑的。我带着几个裂开的茶具去找他,像个病人去找老医生。
老陈拿起我裂开的茶杯,用手指轻轻敲了敲,又对着光看裂痕的走向。“急了。”他就说了两个字。
他带我看他的窑,那是个比我年纪还大的龙窑,顺着山坡修建,像条卧龙。“火是有脾气的,”老陈说,“你不能命令它,得顺着它。”
他让我住下来,跟着他烧一窑。那七天,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“看火候”。原来火苗的颜色会说话——暗红色是它在喘息,亮黄色是它在奔跑,白炽色是它在歌唱。老陈不时从观火孔看一眼,就能知道窑里正在发生什么。
“你看,”他指着一处火焰,“这里火急了,那边的杯子可能要遭殃。”果然,后来那位置的杯子有几个轻微变形。
他教我听声音——柴火燃烧的噼啪声,窑内气流的声音,还有陶器在高温下细微的收缩声。这些声音组成了一首交响乐,听懂了你就是指挥家,听不懂就只能碰运气。
最重要的是,老陈让我明白了“留白”的重要。以前我总想把火烧到最高温,觉得越高越好。他却说:“最高温谁都会烧,难的是知道在哪里停。就像炒菜,大火爆炒之后要转小火慢炖,陶土也需要时间慢慢成熟。”
那一窑出来,完美无瑕。我摸着那些温润的杯子,突然懂了——我之前太执着于“做”陶,却忘了陶器是自己“长”出来的,我只是在帮它们完成这个生长的过程。
回来后,我完全改变了烧制方法。
我不再设定固定的升温曲线,而是根据天气调整——潮湿的雨天,升温要慢;干燥的晴天,可以稍快。我开始记录每一窑的数据:什么泥料配什么釉,在什么温度下停留多久。厚厚的笔记本写了三本,每一页都是经验和教训。
最重要的是,我学会了等待。在关键的600度阶段(水分蒸发)和1200度阶段(釉料熔化),我会停下来,让温度稳定一段时间,给陶土适应的时间。就像不能让一个人从冰天雪地直接进入桑拿房,陶土也会“感冒”。
慢慢地,裂痕越来越少。从十裂七八,到十裂二三,再到偶尔才有一个微瑕。那种感觉,就像终于听懂了陶土的语言,我们能够对话了。
半年后,我烧出了一套月白釉的茶具。那是种很微妙的颜色,像清晨天空将亮未亮时的白。出窑时,它们完美得让我不敢相信——釉面光滑如脂,色泽均匀温润,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。
我把这套茶具的照片发到网上,没想到一下子火了。很多人问能不能订做,说从没见过这么温润的月白色。订单慢慢多起来,我开始专门烧制茶具。
有个客人告诉我,用我烧的杯子喝茶,茶汤会特别柔滑。我笑了笑,没告诉他,也许是因为这些杯子经历过恰到好处的火候,它们自己是舒展的、不紧绷的,所以盛放的茶水也跟着温柔起来。
现在,我的工作室里还摆着那些早期烧裂的陶器。有朋友说该扔了,我舍不得。它们是我最好的老师——每一个裂痕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火的故事,提醒我曾经如何笨拙地想要征服火,最后却学会了与它共舞。
昨天,我又开了一窑。打开窑门的那一刻,晨光正好照进来,那些茶具安静地立在窑里,泛着柔和的光。我拿起一个茶杯,温热从掌心传来,像是活着的温度。
原来,完美的陶器不是被火烧出来的,而是被火孕育出来的。我们总在寻找不裂的秘诀,却忘了裂痕本身也是语言——它在告诉我们,哪里太急了,哪里该停了。就像生活里的那些挫折,其实都是在教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
柴窑还在后院,每当点火时,橘红的火焰跳跃着,我知道,那不只是火,那是另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生命。而每一个从窑里诞生的茶具,都不只是泥与火的结合,更是一场耐心与时间的对话。这场对话,我会继续下去,用一辈子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光标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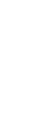 光标文章网
光标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5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0)
2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3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1)
4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7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