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出这件事,其实不是某个瞬间的决定,更像是一滴墨落在清水里,慢慢晕开的过程。
我最早接触写作,是因为孤独。十二岁那年父母外出打工,把我留在外婆家。小镇的夜晚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我就开始在作业本背面写故事——给窗台上的茉莉花编一个前世今生,为隔壁总在黄昏拉二胡的爷爷想象他年轻时的爱情。那些字歪歪扭扭爬满纸张,像藤蔓抓住墙壁,那是我抓住世界的方式。
大学时我在文学社认识了小禾。我们常在深夜的操场边抽烟边聊小说,她说我写的东西“有体温”。后来她成了我的第一任女友,也是第一个读者。我写过这样一个情节:男孩在女孩离开后,收集她抽剩的烟头,把烟纸拆开,用那些焦黄的烟丝在窗台上拼出“再见”。小禾看完哭了,她说:“你把人心里那些说不出的东西都写出来了。”
就是这句话,让我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能写作。
毕业第三年,我的一篇散文意外得了奖。杂志编辑联系我,问能不能开个专栏。那天我激动得在出租屋里来回踱步,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。专栏叫“人间备忘录”,每周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——凌晨四点扫街的阿姨,她口袋里总装着给流浪猫的小鱼干;地铁口卖红薯的大爷,收摊后会坐在台阶上拉一段不再有人听的二胡。
读者留言说:“谢谢你让我看见这些光。”我第一次意识到,文字可以成为桥。
但变化是悄悄发生的。
开始有出版社找我出书,开始要配合宣传写软文,开始计算稿费和流量。我依然在写普通人的故事,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在动笔前会先想:这个题材会不会爆?标题够不够吸引人?编辑说:“你要考虑市场。”我说好。
最明显的是去年写外卖员老陈的故事。我跟他跑了一整天,记录他爬过的每一级台阶,他对每个顾客说的“祝您用餐愉快”,他蹲在马路牙子上啃冷馒头时接到女儿电话瞬间绽放的笑容。但交稿时,编辑说:“能不能多写写他女儿生病缺钱的部分?这样更有爆点。”
我改了。文章反响很好,很多人说看哭了。只有我知道,我删掉了老陈最让我触动的一个细节——送完最后一单,他在河边静静站了十分钟,什么也没做,只是看夕阳。他说:“这一天里,这十分钟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。”
我没写进去,因为编辑说“这个太文艺了,读者不爱看”。
那天晚上,我对着电脑发呆到凌晨。我突然想起十二岁的自己,在作业本背面写下第一个故事时,从没想过谁会看,会有什么反响。写作于他,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
今年春天,外婆去世了。整理遗物时,我找到了那些写满故事的作业本。纸页已经发黄,字迹模糊,但每一个字都那么真实,那么自由。
守灵那晚,我坐在外婆躺过的旧藤椅上,听见隔壁又传来二胡声——还是那首《二泉映月》,只是拉琴的人换成了爷爷的孙子。我突然明白,有些东西在传承,也有些东西永远消失了。
回城后,我推掉了两个商业约稿。编辑很着急:“这可是很好的机会!”我说我知道,但我需要停一停。
不是写不出来,相反,我现在每天还在写。只是不再为发表,不再为谁看。我写早晨咖啡杯里旋转的泡沫,写楼下孩子们跳皮筋时唱的童谣,写梦里外婆对我说的一句话。这些文字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,它们重新属于我自己。
所以,回到最初的问题:我什么时候退出?
我想,从我为了市场删掉老陈那十分钟开始,从我不再敢写“太文艺”的句子开始,从我忘记写作最初只是为了对抗孤独开始——退出就已经发生了。它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决绝告别,而是一点一点地,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,我已经离开了我最珍视的东西。
现在,我在一家小书店做兼职。偶尔有客人认出我:“你是不是那个作家?”我摇摇头:“我只是个喜欢写字的。”
昨天整理书架时,发现一本破旧的《小王子》。随手翻开,看到那句话:“真正重要的东西,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”
合上书,窗外梧桐叶正一片片落下。这个秋天,我想重新开始写作——不为证明什么,不为取悦谁,只为我还能被生活打动,还能为一片落叶驻足。
退出不是结束,是另一种开始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当作“作家”,写作才重新回到我生命中最纯粹的位置。像十二岁那个夜晚,台灯温暖,笔尖沙沙,世界安静,而我的心,无比自由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光标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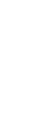 光标文章网
光标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5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0)
2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3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1)
4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7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