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号码,我已经三年没有拨过了。
手指悬在绿色的拨号键上,犹豫着。我知道会听见什么,可还是按了下去。听筒里传来漫长的等待音,一声,两声,然后突然中断——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,请核对后再拨。”
冰冷的机械女声,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我愣住了,握着手机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怎么会是空号呢?明明上周才……
哦,不对。妈妈已经离开三年了。
这三年里,我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——在那些辗转反侧的深夜,拨通这个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。听筒里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声音,像是连接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我会对着忙音说话,说今天工作上的烦心事,说最近看的电影,说楼下新开的早餐店,油条炸得没有她做的好。说我想她了。
这成了我一个人的仪式。不需要回应,只需要知道电话那头,至少在物理上,还有一个号码属于她。可现在,连这个号码都被收走了。
妈妈走得特别突然。心梗,救护车还没到,人就没了。我接到邻居电话时,正在外地出差,连夜赶回去,只见到已经冰冷的她。她走的前一天晚上,我们还通过电话。她说最近学会了视频通话,让我周末教她怎么用滤镜,“听说能把皱纹都变没”。我说好,周末就教她。可她没有等到周末。
整理遗物时,我在她床头柜发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。翻开一看,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所有成绩单的复印件,每一张旁边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她的评语:“这次数学有进步,奖励红烧肉”“语文作文得了优,真棒”“物理不太理想,别灰心”。最后一页,贴着我大学毕业典礼的照片,下面写着:“我的儿子,真了不起。”
我坐在地板上,抱着那个本子,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妈妈是个普通的中学老师,教了一辈子语文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。记忆中,她总是很忙——白天上课,晚上批改作业,周末还要带我去各种补习班。但她从不抱怨,总是笑眯眯的。
她最爱说:“等你长大了,妈妈就轻松了。”
可等我真正长大了,工作了,能让她轻松了,她却没能等到。
刚走的那几个月,我几乎每天都会打她的电话。有时是中午,有时是深夜。电话那头永远是忙音,但我就是停不下来。朋友劝我,说这样不好,人要向前看。我知道他们说得对,可我就是做不到。
直到有一次,我加班到凌晨三点,回到空荡荡的家里,习惯性地拨通了那个号码。这次不是忙音,而是接通了——一个陌生的男声:“喂?”
我愣住了,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:“对、对不起,打错了。”
挂掉电话后,我查了一下,原来那个号码已经被运营商回收,重新投放使用了。从那天起,我再也没有在白天打过。只在深夜,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,才敢偷偷拨一次。我知道这很傻,可这成了我和她之间唯一的联系。
现在,连这个联系也断了。
我翻着手机里的老照片,有一张是去年春节拍的。妈妈系着那条用了多年的碎花围裙,在厨房里包饺子。我站在她身后偷拍,她转过头来,假装生气:“又偷拍我,皱纹都拍出来了。”可眼睛里全是笑意。
那天她包了我最爱吃的三鲜馅,一个个饺子像小元宝,整整齐齐排在案板上。蒸汽从锅里冒出来,把厨房熏得雾蒙蒙的。她说:“明年咱们包点新花样的,学学网上那些。”
明年。我们总以为会有很多个明年。
放下手机,我走到阳台上。天快亮了,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,几颗星星还固执地亮着。楼下偶尔有早起的环卫工人扫地的声音,沙沙的,像时光流逝的声音。
我想起妈妈说过的一句话:“人啊,就像天上的星星。有的亮得久一点,有的亮得短一点。但只要是真心亮过,就会在别人的记忆里一直亮下去。”
她确实一直在我记忆里亮着。
那个再也拨不通的号码,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它提醒我,有些东西真的回不来了。但同时,它也让我明白,有些东西从来就不需要电话来维系。
我回到屋里,打开电脑,开始写这篇文章。窗外的天越来越亮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知道,从今往后,我不能再依赖那个深夜的电话了。我要学会在没有忙音的世界里,继续想念她。
也许有一天,我会把她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。告诉他们,曾经有这样一位外婆,她很普通,却很伟大;她离开了,但从未真正离开。
而此刻,在这个普通的清晨,我对着渐渐亮起来的天空,轻轻说了一句:
“妈,早安。”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光标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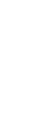 光标文章网
光标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5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0)
2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3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1)
4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7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