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煎饼摊就在老棉纺厂后门那条巷子里。说是摊子,其实就是个改装的三轮车,右边是面糊桶,左边整整齐齐码着鸡蛋、生菜、薄脆,中间那块铁板被磨得锃亮。每天四点起床,调面糊、炸薄脆、切葱花,五点半准时出摊。面糊要调得不稠不稀,稠了摊不开,稀了没嚼头——这个分寸,我闭着眼睛都能掌握。
今天和往常一样,刚支好摊子,第一个老主顾就来了。
“老规矩,两个蛋,多加葱。”
是李工,棉纺厂退休的老钳工。他女儿在南方工作,老伴前年走了,现在每天早上遛弯过来,就为吃我这口煎饼。
“今天鸡蛋新鲜,给您挑个大的。”我舀起一勺面糊,手腕一转,在铁板上画出一个完美的圆。打蛋、摊平、撒葱花,动作快得像在跳舞。这手艺是跟我爹学的,他当年也在这一带卖煎饼,养活了我们兄妹三个。
李工接过煎饼,却不急着走,站在摊子旁边吃边聊:“你这煎饼啊,跟我年轻时在天津吃的味儿差不多。就是少了点甜面酱。”
“您要是想吃,明天我给您备上。”我顺手把下一个煎饼里的火腿肠多煎了会儿——我知道接下来要来的小学生喜欢焦香的。
六点一到,上班族涌来了。小陈总是第一个,这个在写字楼里做设计的年轻人,永远睡眼惺忪。
“王姐,双蛋加肠,咖啡我自带了。”他把保温杯往车把上一挂,“您说奇不奇怪,公司楼下那么多早餐店,我就觉得您这煎饼最对胃口。”
我笑着往他的煎饼里多塞了片生菜。记得有回他加班到凌晨,正好碰上我出早摊,那会儿他眼睛都是红的,却还记得跟我说:“王姐,您这煎饼摊就是我们这片区的灯塔。”
这话说得文艺,但我懂。深夜里,清晨时,总有那么些人在为生活奔波。我的煎饼摊亮着的那盏灯,热着的那块铁板,或许真能给人一点暖意。
七点钟,最热闹的时候来了。送完孩子的妈妈、赶公交的上班族、扫完大街的环卫工...我的两只手像上了发条,舀糊、摊饼、打蛋、翻面、加料、折叠、装袋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铁板滋滋地响着,葱花和蛋液的香气在晨雾里飘出去老远。
“王姐,老样子!”
“多加辣酱!”
“我的不要葱!”
不同的声音在摊前响起,我却能分得清清楚楚。张老师的要脆些,刘阿姨的酱要少,门口保安小赵总爱加两个蛋...这些口味偏好,我都记在心里。有时候他们还没开口,我已经开始按他们的喜好做了。
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,每天都会来买一个最基础的煎饼,不加蛋不加肠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妈妈生病了,爸爸在工地干活,她每天把早餐钱省下一半。从那以后,我总“不小心”把别人的双蛋煎饼“错”给她,收的还是基础煎饼的钱。小姑娘现在考上重点高中了,偶尔还会回来,悄悄在我面糊桶旁边放个苹果。
今天快到八点的时候,面糊桶见了底,鸡蛋也只剩最后一个。我正准备收摊,看见马路对面有个身影急匆匆地跑过来。
是住在前街的老周,跑得气喘吁吁:“还好赶上了!今天孙子发烧,去医院刚回来。”
我看了看桶里剩下的面糊,刚好够一个煎饼的量:“最后一个,给您加个蛋?”
老周连连摆手:“不用不用,基础的就行。”
但我还是把最后一个鸡蛋打了进去。老周的老伴去年癌症走了,那段时间,他每天来买两个煎饼,一个自己吃,一个带给医院的老伴。后来变成一个,他总是在摊前站一会儿,看着煎饼出神。
我把煎饼递给他,他掏钱的手有点抖:“王姐,你说这人啊,忙活一辈子图个啥?”
我没说话,只是把煎饼又往他面前递了递。热乎乎的煎饼在他手里冒着白气,他低头咬了一口,含含糊糊地说:“就图这口热乎的。”
八点整,最后一点面糊用完。我拧灭煤气罐,开始收拾摊子。铁板慢慢冷却,巷子里的晨雾也散了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,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两小时,一百多个煎饼,换来的是兜里那些皱巴巴的零钱,更是这八年来积攒下的人情冷暖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,只知道把面糊摊圆,把火候掌握好,记得每个老主顾的口味。这片街坊养活着我的小摊,我的小摊也温暖着他们的清晨。
推起小车往回走时,隔壁理发店的刘师傅正在开门,朝我喊了一句:“王姐,明天还来啊!”
“来,天天都来。”我应着,车轮又开始咕噜咕噜地响。这声音会一直在清晨的巷子里响起,只要我还摊得动煎饼,只要还有人想吃这一口热乎的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光标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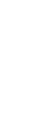 光标文章网
光标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5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0)
2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1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1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7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